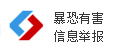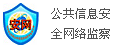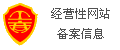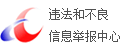|

1.
香港回归那年我7岁,父亲原本开在县城周边的地毯生意,因市场不佳,宣告破产。我们一家七口,便坐着拖拉机晃晃荡悠回到了父亲出生的鲁西南农村。
用风水先生的话说,我们村三面环水,没河的那面照旧下坡路,“生财留不住,官运不亨通”。确实,开国之后我们村独一出过的“官”,不外是县的,说不上什么话。以至于多年今后,爷爷念叨他的叔爷时仍是满脸孤高,“四几年回过一趟家,骑着高头大马,带着保镳”,只是“命欠好,南撤的时候挨了枪子,否则此刻返来,怎么着也得把咱们村弄发家喽”。
出个官,且是个大官,成为村里每一个闯过饥荒的爷爷们心里沉甸甸的但愿。
于是,在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,念书上大学与当官蓬勃,在村里人眼中大抵是划等号的。三叔曾经是村里的第一代“做官种子”,只是三叔“语文还好,数学我一看就犯困,不断打打盹,被你爷爷瞥见就拿棍子抽我”。80年月,三叔委曲考了3年大学,最后啥也没考上,落了个一地鸡毛,狼狈回村。亏得谁人时候只有小学文化的父亲修建生意步入正轨,兄弟齐心,固然没能成为光宗耀祖的“官”,至少也是村里数得上的鲜明人家。
二华子是村里念书做官第二代种子。
与三叔差异,二华子从小进修后果就很好,“脑瓜子智慧,算账快”,在周边几个村落合办的小学里,后果出类拔萃,一直被认为会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。比及初中结业,二华子一鼓作气考上了其时县里最好的中学——县二中,更成了村里人眼中前途无量的“准大学生”,以及终于能走出去的“官”了。
当时候村里人盼自家孩子成才,总拿二华子作类比:“天天天还不亮就起床,怕花家里电费,别管天冷天热,在院子里借着天亮读书,你没人家那脑筋,跟人家一样尽力也行。”
我堂姐和二华子同岁,除了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,烧水做饭,农忙时节还要下地捡麦穗、拾花生,即便这样我大姐仍然是爷爷眼里要嫁出去的“赔钱货”、“上不上学没啥用”。
以至于,多年后远嫁北京的堂姐回家探亲,依旧满是委屈:“人产业官的哪个不是方面大耳,一脸官样,哪像二华子又丑又矮,除了死读书啥也不会,连饭都要他娘给他摆上桌,眼睛跟长到了头顶上一样,在村内里走,别管见谁连声号召都不打……”
二华子上面有个哥哥,早年病没了,除此之外只有一个姐姐。二华子从小备受痛爱,稀有的没有像同龄人一样从小在地里“像庄稼一样长大”。用村里人的话说就是,“下地除草,能把一垄垄的麦子除去,回家还说本年地里草太多”,虽然了,“不会种地怕啥,二华子又不是农夫,未来读大学是要出去做官的。”
2.
1993年二华子第一次高考 “发挥反常”,复读一年高考的时候闹肚子,比及第3年告急地睡不着觉,连科场都没有进,二华子的父亲就积极撺掇他再考一年,二华子却果断差异意。
反倒比二华子低两个年级的我堂姐,在复读一年后考上了东北农大,成了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,这下村里炸开了锅,各人加倍相信“人在世都是命”。
自家孙女考上大学,我爷爷却兴奋不起来:“学农业有啥用,回家种地使吗?闺女迟早是人家的人,咱们村风水欠好……”
我也是当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二华子。
村落最东边尚有一片晒麦场,平整平滑,村里人喜欢三三两两聚在这里,聊谈天、打打牌,说些老家话。我们回乡那天,二华子就坐在晒麦场旁边的石碾子上,穿戴无袖白背心、大裤衩,戴着眼镜,瘦怯怯的,与周边光着上身摇蒲扇的汉子们截然差异,倒和刚回抵老家的父亲差不多。
二华子周围没有大人,只是围了一群小孩子,往返撺掇:“二华子,讲一个嘛,讲一个……”
我这才知道是他,一时间却又不能跟“二华子”这个名字划上等号——想象中的他应该是一个年青有为、西装革履的乐成人,脑门锃亮,一脸智慧样。
二华子先故作嫌弃:“不讲不讲,哪有每天讲嘞,肚内里就这点对象,讲完就没有了。”
小孩子们却不依,吵喧华闹,直到周边打牌的大人们被人厌狗憎年龄的孩子吵得不耐心,才不耐心地带着训斥开口鼓舞:“二华子,你屁事没有,就给他们讲一会。”
|


 主页 > 口述实录 >
主页 > 口述实录 >